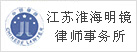作者 李永田
(一)
于学强先生的散文集《暮年笔耕情》即将付梓。耋耄之年,再推大作,犹如老年得子,可喜可贺!
书中的篇章,或写人,或记事,或抒情,或记游,或议论,无不是作者真情实感的心灵剖白。
鄙人虽也乐于舞文弄墨,但其实並不谙散文的写作之道,只牢牢记住了少年時老师说的一句话:“散文也者,形散神不散也”。
于是,我便在这部《暮年笔耕情》中,苦苦地寻觅着它的“神”。
蓦然之间,从“自序”之中、从书目之中、从范文之中,涌现出了两个大字:时代、时代与时代!
是啊,我们生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伟大時代。这部书,就是勇立時代之潮头的弄潮儿,精心采撷下來的時代潮流之中的朵朵浪花,就是作者对这个時代的热烈的讴歌和赞美,就是作者向伟大時代真情地呈献出的一份厚礼!
从形式上看,它是一部散文的结集;从内容里看,它是一曲对時代的激情赞歌;再细细思量起來,它乃是一部百年变局的時代史诗!
(二)
于学強先生在本书的自序中,坦言自己是一名“幸运儿”,理由是幼年写作的兴趣与成年后的记者生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,终生都在从事着自己挚爱的事业。
其实,出生于这片神州热土、生活在这个伟大時代,没有战乱硝烟、没有重大疾疫、没有饿殍载道、没有盗贼猖獗,红旗飘飘,国泰民安,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強起来的我们这些中华儿女,应该说,人人都是幸运儿。
尤其幸运的是我们这些“四O后”们:在民族危亡的险境中出生,在凯歌高奏的红旗下成长,在艰难困苦的時日里求学,在运动频仍的环境里求索,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拚搏,在和谐盛世里安享晚年。
我们不相信有什么“命运之神”,但確实有一颗“幸运之星”总在眷顾着我们:抗美援朝出兵時我们还小,对越自卫反击战時我们已老;晚生了几年,我们躲过了“反右”災祸,早生了几年,我们没有加入“上山下乡”的大军;文化大革命开始,正值我们青春年少,实行“计划生育”后,我们的儿女已在膝下萦绕……
于学強先生生于1945年,妥妥的一个“四O后”。他书中林林总总的文章,不仅仅是自己的经历和感悟,也是我们四O后们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心声。
感谢于学强先生用他生花的妙笔,代表我们这些人,写出了我们的追求、我们的希冀、我们的爱恋、我们的奋斗,乃至于我们的苦厄、我们的挣扎、我们的呐喊。请注意,这里没有绝望、没有艾怨、没有消沉!
(三)
我们这个年纪的人,是戴着红领巾和团徽长大的,骨子里融入了時代的正能量,担负起共和国大厦建设的重任。
我们将自己全部的忠诚和智慧,奉献给这片养育了我们的土地,上无愧于天,下无愧于地;外无愧于人,内无愧于心。于学強先生就是我们同皊人的代表,《暮年笔耕情》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品格的写照。
请看,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深沉。
对父母的爱,请看《忍辱负重的一生》,赤子之情,溢于言表;对妻儿的爱,请看《牵手走过57个春秋》,夫妻恩爱,忠贞不渝;对故土的爱,请看《囬望故乡》,溯源寻根,一往情长;对天地的爱,请看《大美徐州,与花相约》,天人和合,草木有情;对祖国的爱,请看诸多神州名胜的游记。还有,对生活的爱、对事业的爱、对朋友的爱、对人民的爱、对人类的爱、对寰宇的爱,无不在书中各个篇章中,闪现着耀眼的光彩。
大爱无疆,地老天荒。人生苦短,惟爱绵长。献出大愛,与日同光。
正是心胸之中充滿了这些滔滔奔腾的大爱,才使得作者坐卧不宁,不吐不快,勤奋笔耕,不知老之将至。
天道酬勤,地道酬真;人道酬善,文道酬新!作者心中之爱流淌到笔端造就的篇篇美文,正是我们这个時代最需要的勤、真、善、新啊!
(四)
历史的河流是如此的漫长,而人生的行程却是无比的短暂。
我们何其有幸,生活在世纪之交的時代,由煤油灯下的苦读,到电灯电话的欣喜,再到衣食住行的无忧,再到互联网和AI的飞跃,世世代代仁人志士悠远的中国梦正在我们的身边成为现实。
短短的人生中经历了几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梯,历史在这里前行的特别急速,几十年间便经历了沧桑巨变。
如前所述,我们是共和国的建设者,而同時,我们又是時代前行的见证人。我们的先人,一代又一代,面朝黄土背朝天;我们的后人,尽享现代化的恩赐,只能在教科书里看到困苦与艰难。从这个意义上來说,我们这一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!
于学強先生一生从事新闻工作,对時代的变迁感触更加深厚,从而在这本书中更加全面和真实的反映出來。
本书中有一篇文章,题为《贾汪真旺的见证者》便是明证。
世人尽知,杭州的西湖美不胜收,“若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。谁人知晓,在新時代里,一位旷世美男子——潘安,出现在淮海大地,向绝美的西施挥手示爱。
这便是徐州贾汪的潘安湖!
这里原是权台煤矿和旗山煤矿的采煤塌陷区,伤痕累累、滿月疮痍,是英雄的徐州人民将之打造成一个国家4A景区,推出了一个潘安重生的神话。
总书记2017年到这里视察,赞扬“贾汪真旺”,並在潘安湖畔的马庄买了一个香包,成为淮海大地的一个美谈。
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。作者的第三故乡贾汪的沧桑巨变,便折射出徐州的巨变,折射出美丽中国的蝶变。
在大变革的時代里,稍不留神,便会落伍。而我们的学強先生正如他的名字:学強学強,学強则強。強者无忧,强者无畏,強者无敌!他勇立時代之潮头,纵观风云之变幻,速记惊雷之声响,发出時代之強音。
我为之点赞!
(五)
本书的书名为《暮年笔耕情》,突出了“暮年”两个字。我想对此作一个诠释。
作者在这里所指的是“生理年龄”:人生七十古来稀,作者年届八十,垂垂老矣。
其实,人还有一个“心理年龄”:智者是没有暮年的。但得夕阳无限好,何须惆怅近黄昏?
请读者打开书页,通篇读一读书中的文字,似乎到处是鲜花,到处是美景,到处是诗情画意,到处是青春热情的迸发。哪里找得到晚年的凄凉、夕阳的悲叹、日暮的惆怅、黄昏的惊恐?
假若说有什么不同,那也是因为年龄的增长,生活的积累,岁月的钩沉,让文字更加深沉、更加通透、更加老辣!
出书,对知识分子來说是一件大事。老人出书,远离了“功利”的羁绊,既不是为职称的评定,又不为世俗的邀功行赏,更不为区区的稿酬,只为给世间留一份情、给時代添一抹彩、为子孙积一些德,因而更值得人们赞誉。
算起來,学強先生今年整整80岁,是谓“木寿”。近期目标,应该是“米寿”——88岁。远期目标,则是“茶寿”——108岁。到那時,我们的祖国“两个一百年”的目标已经达到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实现。
來日方长,愿学強先生笔耕不辍,有更多的大作面世。
我愿做一名忠诚的读者。汝为時代添彩,吾为先生鼓呼。南來北往,以文会友,实为人生一大幸事,更是晚年一大乐事!
2025年9月8日于北京
作者简介:
李永田,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,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,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。
 苏公网安备 32031102000168号
苏公网安备 32031102000168号